弘扬潮汕文化 传播民族影音 振兴潮汕艺术 凝聚民族精神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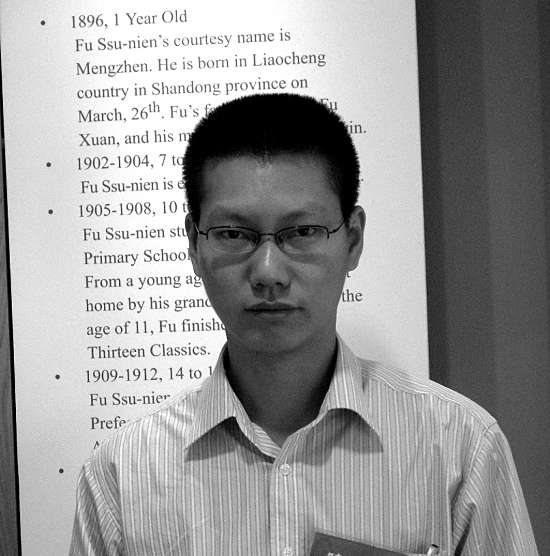
如果没有与陈壁生教授有过接触,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位年轻人身上有如此深厚的国学底蕴。这次难得的采访机会,更是让记者深刻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、潮汕文化的由衷热爱。
研究潮汕宗族和信仰
继承中国文明传统最核心是经学学国学可以更科学认识潮汕文化
《汕头日报》:请介绍下您的个人简历和在学术方面的研究重点、取得的成就等。
陈壁生教授:我出生于1979年,潮阳关埠镇东湖村人。在潮汕地区度过童年、青少年阶段,2002年在汕头大学法学院毕业,拿了法学学士学位,2007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,取得哲学博士学位,毕业后北上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书至今。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经学,这和我读的哲学有很多的交叉,至今出版过几本小书,如《激变时代的精神探寻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)、《经学、制度与生活——<论语>“父子相隐”章疏证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)等。现在除了做专业研究和教书,也研究潮汕文化,尤其是潮汕的宗族和信仰。
继承中国文明传统最核心是经学
《汕头日报》:国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?您为什么会涉足国学的研究领域?传统的潮汕文化对您的影响大吗?
陈壁生教授:“国学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,但是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对象,即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因为前几年开始,有所谓“国学热”,对国学的认识五花八门。我在念哲学的时候,人家问我读什么专业,我说读哲学,对方基本上不会再接这个话题;等到我工作之后,人家问我在什么单位教书,我回答国学院,绝大多数人马上会说:“我对国学很有兴趣!”甚至有不少人开始问我会不会看风水。很有意思,这看出社会上对“国学”的一般看法。从专业的角度来说,国学比较讲究经史子集的贯通,但这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达到。民国时候,有人称京剧是“国剧”,武术叫“国术”,仿佛什么东西戴上一个“国”帽就身价百倍。其实看历史上被称为“国学大师”的学者,像王国维、陈寅恪,乃至于今天潮汕的骄傲饶宗颐先生,研究的都是非常专门的学问。
我之所以会从事国学研究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,是我觉得国学,尤其是其中的经学研究,在中国已经中断了近百年,我们今天要继承中国文明传统,最核心的就是经学。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,最重要的也是经学。今天应该重新去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文明。
当然,我这些想法,跟自己的生活经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从小在东湖村长大,整个村子有一个共同的先祖,虽然祠堂已经改成了学校,但聚族而居的生活,让人觉得温情脉脉。人生活在家里,在自然之中,在土地之上,这才是真正人的生活。在二十年前,我完全无法想象人可以在高楼大厦之中活着,周围全都是陌生人。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群体之中,传统上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关系都被彻底瓦解了。当我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思想与历史,很快发现,那样一个中国,才是我童年生活的源头。
学国学可以更科学认识潮汕文化
《汕头日报》:在浮躁的当今社会,您认为学习国学最需要什么?学习国学有什么现实意义?
陈壁生教授:学习国学最需要什么?对不同的人回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对想学国学的大学生,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担当的精神,坐得住冷板凳,从《十三经注疏》开始,好好读书。如果是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,我建议他们多看看史书,特别是古代那些著名的官员的修身之道。
国学是最古老的知识,却也是最具现实感的知识。一个认真读过《论语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的人,和一个没有读过的人,在精神面貌、气质、见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国学对当代中国人的个人修身、治理一地一国,都有重要的意义。举例来说,我认为在中国当代的政治体制中,每一个科级以上的地方官员,都应该接受地方文化培训,主要内容是阅读本地历史上重要的县志、府志。只有懂得了一个地方的历史,才能热爱这个地方,理解这个地方的现实,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将会怎样写进历史之中。
对潮汕地区而言,如果学习国学,会发现潮汕文化直到今天,仍然保存了中国文明的许多精神。在潮汕地区,从我有记忆开始,每家每户在先祖的忌日、时年八节都要在自己家里“拜老公”,其实这就是《礼记·王制》中所说的“庶人祭于寝”。潮汕地区近年开始复兴的祠堂祭祀,更是对宋、明之后的祖先祭祀的回归。另外,潮汕的许多俗语是中原古语,许多音调是中原古音,像潮语称公共厕所为“东司”,如果读宋朝人的笔记,便会发现这原来是宋朝的话。可以说,对潮汕人而言,学习国学,可以更理性、更科学地认识潮汕文化。
城市魅力在于深厚文化内涵
《汕头日报》:您觉得文化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重要吗?
陈壁生教授:文化对一个地方的发展,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一个群体的基本特征,是文化所塑造的,而一座城市的魅力,表现在她的那些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的载体上。例如,对广州而言,如果没有南越王墓、陈家祠,没有康有为、孙中山,这座城市会失去多少魅力!对潮汕人而言,汕头的小公园,潮州的湘子桥与韩祠、孔庙,揭阳的进贤门,潮阳的文光塔等等,都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,这些文化的表征,是城市的名片。在艺术、生活方面,像潮语、潮汕建筑、潮剧、工夫茶、潮菜等,都曾经构成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。
在今天“现代化”、“全球化”背景下,几乎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走向衰落,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。文化之于一地,就像灵魂之于生命那样重要。尤其是在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,不管是满足于现实还是对现实不满的人,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组织,都应该看到,构成我们共同生活方式的那些文化因素,是最可宝贵的,传统艺术、建筑,一旦消失,便成绝响。事实上,我们今天的潮汕口语,跟几十年前相比,已经极大程度书面化了,许多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表达,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彻底消失。一个词汇的消失其实就是它所表现的那种情感的消失。
改造小公园最重要是恢复旧貌
《汕头日报》:对于汕头来说,您认为在文化弘扬与创新方面应该怎样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?
陈壁生教授:对汕头而言,政府部门在保存、弘扬这座城市的文化传统方面,应做得更好,而民间的宗族、慈善组织,做了非常多的努力。包括重建祠堂、进行慈善事业、传播地方文化等方面。比如,许多的村庄都重修了祠堂,有的还恢复了祭礼,在潮阳城区,有萧氏“四序堂”、姚氏大宗祠、郑氏孔安堂等祠堂,这些祠堂不但是一姓祭祀的场所,祠堂建筑本身就是潮汕建筑文明的结晶,而且,祠堂还常常承担了助学、慈善等公共化的功能。在汕头市区,有存心善堂等机构。对于民间保护、弘扬传统文化的努力,政府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予以支持。
汕头市政府近期继续进行以小公园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建设,说明了对汕头历史文化的保护,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的一致共识。汕头开埠百余年,根基便在老城区,以小公园为中心的老城区,承担了汕头人共同的历史记忆,而现在也确实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措施进行保护的最后时刻。旧城保护,在中国各大城市已经有很多先例,但有成功有失败。我觉得对汕头小公园一带的旧城改造而言,最重要的是恢复旧貌,恢复旧貌就是恢复这个城市共同的集体记忆。如果过于追求商业利益,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既破坏了老区旧貌,又无法吸引市民与游客。
考察那些旧城保护比较成功的例子,有几个方面值得借鉴。第一,老城是活的而不是死的,即要保护原有居民的生活,而不是把现有居民都赶走。第二,以尽可能原汁原味的旧建筑、潮汕小吃等等,吸引游客。第三,可以在修复的旧城之中适当建立博物馆,宣传潮汕文化与汕头开埠历史。第四,应该着重突出文化意义,以文化带动旅游。而在文化上,潮剧、潮绣、剪纸等等,都可以在老城展示出来。
年轻人要珍惜地方文化传统
《汕头日报》:作为祖籍汕头的在外年轻学者,您关注家乡的发展吗?对于家乡的年轻人,您最想跟他们说什么?
陈壁生教授:就我的了解,许多在中国各大高校工作的潮汕籍学者都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,我也不例外。对于家乡的年轻人,我想说的是,潮汕有着优秀的地方文化传统,要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。
本报记者 陈静莹
